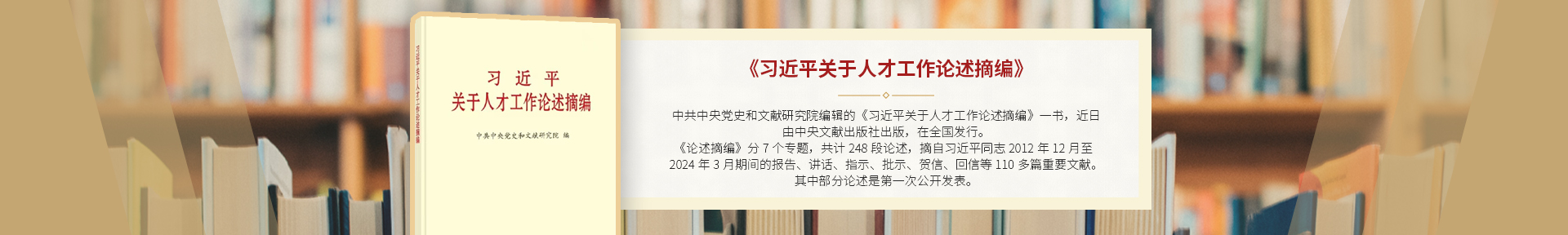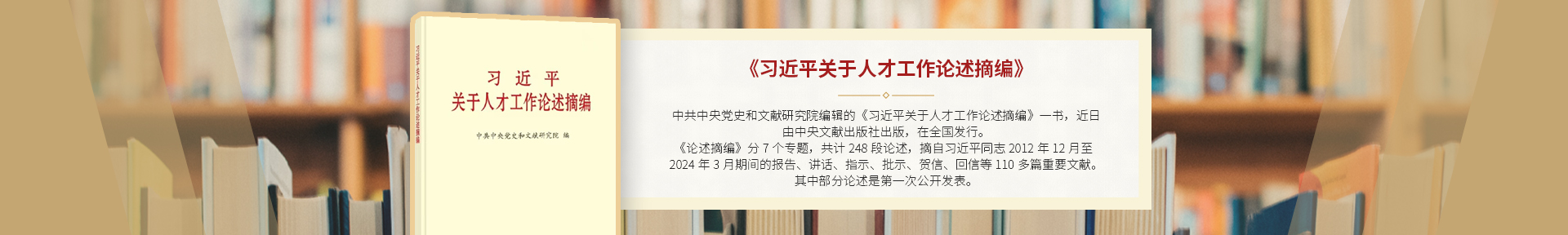毛泽东谈韩愈与柳宗元——读《毛泽东年谱》札记之六
发布日期:2021-02-25
《毛泽东年谱》记载,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与复旦大学刘大杰、周谷城谈话,内容包括学术讨论、中国文学史、京剧现代戏、教育改革、《辞海》等问题,年谱上仅摘录了关于学术上争论的问题,毛泽东对周谷城说:
“你们不要怕批评,要有批评才能进步,不是我们叫人家来批评你,而是群众自发地来批评你。这次批评了你一下,对于大家都有好处。目前你暂时且慢写文章,等他们不再批评你了,你再把他们的文章拿来好好地看一看,做一些研究。他们讲得对的地方,你应该接受,做些自我批评;有些地方如果你觉得可以辩论,你还可以再写文章同他们辩论。在逻辑问题的争论中,我同意你所主张的要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区分开来的意见,我倒不同意把两者混淆起来的论点。形式逻辑,讲的就是形式,那就是关于思维形式的法则嘛。”
毛主席这里讲了二个问题,一个是对待学术争论的态度,在学术问题上可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抱冷静客观的态度,不要急于回答,仔细推敲,分清是非以后,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嘛,有的问题一下子也难以说清是非,各人的视角不同,那可以百家争鸣,保留各自的不同意见。争论的双方要互相尊重对方的人格,不能以辱骂为事。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毛泽东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比较倾向于周谷城先生的观点。我记得首先起来批评周谷城先生文章的是复旦政治课教研组的一个教师沈秉元,他的文章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他文章写好以后,曾拿来征求过我的意见,询问我是否可以拿出去发表,我看过他的文章,说过这是属于学术讨论的问题,可以争论,不要用批判的口气,尽量用商榷的态度。当时我是鼓励他把文章拿出去,可以活跃一下学术空气。他是一个青年教师,很胆怯,害怕引起什么问题,我说这类问题与政治问题是二回事,是思维方法的问题,辩证法与形式逻辑是研究问题的二个不同的范畴,有联系,也有区别,既不能割裂,也不能混淆,这场争论便是这样开始的。
毛泽东在与周谷城谈论正确对待学术争论的问题之后,与刘大杰进行了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谈话,毛泽东说要看刘大杰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并说以后你再有书出版一定要送我一部。刘大杰向毛泽东提出文学史方面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说:
“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韩愈的诗文有点奇。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柳宗元的文章思想性比较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柳宗元顶多可以说有些朴素唯物主义成分。刘禹锡的文章不多,他所作《天论》三篇,主张‘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之说。他反对迷信。刘禹锡可以说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宋朝的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宋神宗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不容易做到。我们要学习王安石这种精神,不要害怕批评,要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见解。”
毛主席随口讲中唐几个文学大家的特点,以及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讲得非常贴切。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说他文起八代之衰,他改变了骈体文那种形式主义之辞藻堆砌特色。韩愈在文字上喜怪而尚奇,若其古诗《忽忽》:
“忽忽乎余未知为生之乐也,愿脱去而无因。
安得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合。
绝浮沉,死生哀乐两相弃,是非得失付闲人。”
此诗其奇特犹如庄子之《逍遥游》所显示的鲲鹏之志。韩愈古诗好以奇特怪僻取胜,但其近体诗作亦有意境浑厚之佳作,若其后期在元和十四年被贬潮州刺史,在赴任至蓝关时,写了一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他的侄孙叫韩湘,一路陪伴韩愈同行。今录其诗于下: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此诗沉郁顿挫,万般感慨,此处所言朝奏指他的《谏佛骨表》。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佛指骨一节,元和十四年,唐宪宗遣中使杜英奇迎佛骨,押官人三十,持香花,迎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佛祠。这在当时为一盛事,那时韩愈是刑部侍郎,上疏谏止,这封朝奏便是《谏佛骨表》,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这一段文字刺痛了唐宪宗,欲其抵死,是裴度为韩愈说话,才贬潮州刺史。诗的首句是交代全诗的背景,那年他已经五十二岁,他宁肯以衰朽残年之身,以为圣明除弊事,显示其倔强不屈的性格,后面“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是写离京时的情境及路途之艰难,若把诗与文联系起来读,则诗与文俱佳。
毛主席晚年喜欢的是韩愈的古诗《石鼓歌》,年谱记载1973年8月上旬,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刷大字本的编目中有韩愈的《石鼓歌》(附《石鼓文》),这个任务他是通过姚文元下达给我们的,是谭其骧老师注和译的,并加以说明。全文中引起毛主席喜爱的也许是这几句:
“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
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
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淚双滂沱。
忆昔初蒙博士征,其年始改称元和。”
石鼓文是唐初在天兴(今陕西凤翔)出土,当时误以为是周宣王时的文物,是四言古诗,韩愈对石鼓文评价极高,以此嘲笑孔子编《诗经》时没有西入秦,故不知有石鼓文其事,《诗经》中的大雅与小雅中的作品都不如石鼓文,摭拾了星宿却遗漏了羲娥。羲,指羲和,相传为太阳神;娥,指嫦娥,相传为月中仙女。此处的羲娥意指日与月。关于《石鼓歌》和《石鼓文》容我以后再作详细的介绍。
有关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毛泽东是有保留的,1975年6月18日,毛主席听北大中文系讲师芦荻读苏轼的《潮州韩文庙碑》,该文称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朱注:今录此句前后文:“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毛泽东不赞同苏轼的评论,苏轼所言之八代,谓两汉魏晋南北朝,故他对芦荻讲的那一番话皆由此而发。)年谱记载毛泽东说:
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连苏轼自己在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还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曹操那时候打下的基础。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这是他的高明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动乱,大分裂,这不好,但当时的另一个方面是,南方的广大沃土,全面地得到了开发,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了。这是经济上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后,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做样子,扩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苻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到了他的意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发展。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很有名。玄学的主流是进步的,是魏晋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作家。什么“道溺”!我送那时两个字,叫“道盛”!苏轼说那时期“文衰”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可以把那时的作品摆出来看一看,把《昭明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拿出来看一看,是“文衰”还是“文昌”,一看就清楚了。我再送那时两个字,叫“文昌”。
毛泽东这一番评论,对传统的观念带有颠覆性的影响,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与鲁迅的思想是相通的,他对韩愈的文章和其中表达的观念是有分析的,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否定的一面,而否定的一面主要是他以道统自居。在对韩愈的评价上,他与苏轼的出发点不同,苏轼是从儒家的道统出发,毛泽东是从反道统的视角出发,这一点他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是一以贯之的。这也许是他作为革命者的情怀,至死不渝。
毛主席对柳宗元比较关注,后来还专门让我们将其所作《封建论》、《咏荆轲》注释为大字本,此为后话,暂且不提。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刘大杰说的“柳宗元的文章思想性比韩愈的高”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呢?我们可以从韩柳二人的交往和诗文往来可以对他们的思想性做一些比较。
唐宪宗元和八年春,韩愈作《进学解》,此前他当了三年国子博士,相当于现在大学教授吧,对此他有一点牢骚。《进学解》是一篇哭穷的文章,他说自己的境况是“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博士的生活尚且处于这种窘迫的状态,何以教人?意谓为师者尚且如此窘迫,何以使弟子能信从自己呢?那时执政者李吉甫览其文而怜之,奇其文才,改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那时监修国史的正是李吉甫,但韩愈对作史官兴趣还是不高,毕竟国子博士与史馆修撰两者都是没有权势的部门,而修史更是容易得罪人的行当,故他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一文中,大叹修史之难,认为修史的人都没有好结局,他在文章中说:
“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氏,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一足;崔浩、范晔赤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死;足下所称吴兢,亦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
他作为史官,修当代史,表示自己顾虑重重。他讲到自己之所以成为史官的原因:
“宰相知其无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穷,龃龉无所合,不欲令四海内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职荣之耳,非必督责迫蹙令就功役也。贱不敢逆盛指,行且谋引去。”
至于具体修史之事,他说:
“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万世乎?若无鬼神,岂可不自心惭愧;若有鬼神,将不福人。仆虽騃,亦粗知自爱,实不敢率尔为也。”
这是他讲写作当代史处境之难,这也是实话实说,但他只是为自身打算,境界不高,这实际上是一篇发牢骚的文章。韩愈在史馆任修撰只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编撰了《顺宗实录》五卷,他进实录是在元和十年,那时李吉甫已去世,所以还是遇到了麻烦。陈寅恪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中曾说:“唐代自中叶以后,凡值新故君主替嬗之际,宫禁之中,几例有剧变,而阉宦实为此剧变之主动者,外廷之士大夫,则是宫禁中阉宦党派斗争时及决胜后可怜之附属物与牺牲品耳!有唐一代之政治史中,此点关系至钜,特宫禁事变,外间本不易知,而阉人复深忌甚讳,不欲外廷有所闻得。”而韩愈修撰《顺宗实录》的内容适值半年多时间内发生德宗与顺宗、宪宗之间的帝位更迭,也就是阉宦党派斗争的产物。顺宗、宪宗之间的关键人物是俱文珍,韩愈当年在汴州,曾任节度使董晋属下之观察推官,而俱文珍在那里任监军,他们之间有一段时间在汴州共事。德宗贞元十三年,俱文珍回京师,韩愈曾为文与诗送俱文珍,题为《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诗中称赞俱文珍云:“奉使羌池静,临戎汴水安。冲天鹏翅阔,报国剑铓寒。”序文都是推崇俱文珍功绩之言。有这一层共事的关系,韩愈后来当然得到俱文珍的信赖。德宗是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去世的,顺宗在此前已中风不能言语,德宗去世以后顺宗即位,是王伾、王叔文用事,至八月间,俱文珍联合一部分宦官发动政变,逼顺宗立太子为帝,顺宗为太上皇,宪宗改元为永贞元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贞事变。接下来便是贬王伾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马,王伾病死,王叔文赐死,贬韦执宜为崖州司马。之后是王叔文之党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皆贬为诸州之司马,二王八司马即是这次事变的牺牲品,次年正月顺宗去世,宪宗改元为元和,《顺宗实录》所记即这很短一段时间内的历史事件。韩愈是受李吉甫之委托改撰韦处厚所撰之《顺宗实录》三卷,将其改修为《顺宗皇帝实录》五卷,其所记禁中事当是此前俱文珍告知韩愈的,他在当时所言事件的细节是为俱文珍他们记功的。但宪宗之死,亦出于宫庭政变,为宦官陈宏庆等所弑,“内官秘之,不敢除讨,但云药发暴崩。”(《旧唐书·宦官·王守澄传》)故宦官权衡自身之利害,不愿禁中之事太直白于世,这也许是韩愈意料之外的后果吧。故《新唐书·路隋传》称:“韩愈撰《顺宗实录》,禁中事太切直,宦竖不喜,訾其非实,帝诏隋刊正。”结果是“有诏摘贞元、永贞间数事失实,余不复改。”所谓“宦竖不喜”,“贞元、永贞间数事失实”,无非是指宦官俱文珍在禁中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尽逐二王八司马那件案子,在这次事件中,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司马,未至又被斥为朗州司马。对于这次事变,毛主席是同情二王八司马的。韩愈编撰的《顺宗实录》五卷,所以引起宦竖他们不高兴,尽管韩愈不满王伾、王叔文之行事,但他还是比较忠实地记述了二王八司马的改革事宜及宦竖们发动的这场宫廷政变的经过,故修改的仅限于贞元、永贞间数事。文宗已是宪宗的孙子了,而事变是其祖父即位前后的事。如果回过头来再看韩愈写那篇《答刘秀才论史书》,碰到这样的难题,也难怪他感叹“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他在这封信的末尾讲:“仆虽騃,亦粗知自爱,实不敢率尔为也。”然而他还是认为:“圣唐钜迹,及贤士大夫事,皆磊落轩天地,决不沈没,今馆中非无人,将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后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他将编史的事,寄希望于后学,由此可见韩愈确有个人利害出入的思考。这封信是元和八年十二月写的,柳宗元在次年的正月,写了《与韩愈论史官书》,对韩愈提出批评。
如果把韩愈的那篇《答刘秀才论史书》与柳宗元所写的《与韩愈论史官书》对照来读,可以看到,韩愈的文章尽管写得很潇洒,在文章中处处都流露出一种为个人打算的尾巴,在《进学解》一文中的牢骚亦是如此,有一点个人的小九九在其中,文章的目的多多少少有为自己谋仕途的愿望。韩愈许多给执政者的书信中,都有个人谋取仕进的意图。而柳宗元的文章则堂堂正正,直道而行,论述史官应有的品德,有理有据,是正道,全文对韩愈文中观点步步紧逼,不留任何回旋余地。两相比较,柳宗元的文章在思想性上要高于韩愈,故毛主席对韩柳二人文品比较的论断非常精辟。同样位列唐宋八大家,就文章的才气而言,韩愈确实不俗,在当时的影响要超过柳宗元,但论思想品味,则柳宗元要高出韩愈一筹。不仅这二篇文章的对比是如此,其他文章也是如此,从思想性的品味上讲,柳宗元在唐宋八大家中应是独居魁首的佼佼者。
应当说韩愈在元和八年三月居史官位有这样的顾虑还是可以理解的,韩愈接受李吉甫让其重修韦处厚《顺宗实录》三卷的任务,应在元和八年的十一月,那时俱文珍已去世,故其敢于直书其事了。元和十年韩愈在《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一文中讲:
“修成《顺宗皇帝实录》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奸佞,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讨,比及身殁,尚未加功。臣于吉甫宅取得旧本,自冬及夏,刊正方毕。”
李吉甫是元和九年十月去世的,进实录的表状是在元和十年夏,那么韩愈修撰实录的具体时间应在元和九年春夏时期,而柳宗元那篇《与韩愈论史官书》的时间是在元和九年的正月二十一日。韩愈《顺宗实录》五卷在文宗时引起“宦寺不喜,訾其未实”的反响,说明韩愈对永贞革新与贞元政变多少还有一点秉笔直书的倾向,真正把修史的重担压在韩愈肩上,他并没有因“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而“不敢率尔为也”。至于他在接手前有那么多顾虑,说几句心中的担忧,也就可以理解,他毕竟还是负起一个的史官必须承担的职责。
柳宗元还曾写过一篇段秀实逸事,而且还上逸事于史馆,也正是元和九年之事。段秀实事迹与颜真卿相似,抗击安史之乱有功,后被朱泚所杀,赠太尉。故《新唐书》将其传与颜真卿列于同一卷,柳宗元写《与韩愈论史官书》的直接动因,是为了使段秀实的事迹弗被隐匿。《旧唐书》与《新唐书》之段秀实传,其史料皆取自柳宗元所状之逸事。《新唐书》在传末赞曰:
“唐人柳宗元称:‘世言段太尉,大抵以为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非也。太尉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许人,谅其然邪,非孔子所谓仁者必有勇乎!”
可见柳宗元写此逸事,是为了表彰忠义,他写了《与韩愈论史官书》之后,复作《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其中有云:
“太史迁死,退之复以史道在职,宜不苟过时日,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苐不能竟其业,若太尉者宜使勿坠。”
事实上韩愈并没有辜负柳宗元的期望,《新唐书》之《段秀实传》赞语可为佐证,段的行状所以能在史馆被保存下来,韩愈功不可没。柳宗元、韩愈二人对于史官职责的论述和其实际的作为,对于当今之史家也是一种鞭策吧!
韩柳之间关于师说之争论那是各有千秋了,韩愈在《师说》一文,讲的是为师之道,是传道授业解惑,韩愈讲师道有强出头的意图在内。柳宗元讲的是不敢有为人师之名,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譁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柳宗元已身在贬所,不想再匿祸绕身。柳讲的是他处境的实际状况,故二者各有千秋,但在后世传诵的还是韩愈的《师说》。实际上柳宗元自视甚高,其在《师友箴》中称“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仲尼是指孔子,牙是指鲍叔牙,他自己不似,也没有这样可师可友之人。韩愈写过一篇《毛颖传》曾受人奚落,柳宗元则写了一篇《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毛颖传》本来是一篇游戏而作的小品文,韩愈却因此而受人非议,柳宗元则认为:“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写文章本来也应“有息焉游焉之说”,文章也是“有所拘者,有所纵也”,“韩子之为也,亦将弛焉而不为虐欤,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韩柳作为学者,二人不因人事的变化,始终互相切磋,保持良好的友谊,应是当代学者的榜样。
元和十四年十月,柳宗元卒于柳州,韩愈作《祭刘子厚文》,其文之末云:
“嗟嗟子厚,今也则亡,临绝之音,一何琅琅,徧吿诸友,以寄厥子。不鄙谓余,亦托以死,凡今之交,观势厚薄,余岂可保,能承子托。非我知子,子实命我,犹有鬼神,宁敢遗堕。念子永归,无复来期,设祭棺前,矢心以辞。呜呼哀哉,尚飨。”
话也说得很诚恳,他还为柳宗元写了墓志铭,介绍了柳宗元的生平,赞扬柳宗元与刘禹锡之间的关系,是“士穷乃见节义”,这是指柳宗元因刘禹锡之母年老,奏请与其交换贬所之事,《旧唐书·柳宗元传》云:“元和十年,例移为柳州刺史,时朗州司马刘禹锡得播州(治所在今贵州遵义)刺史,制书下,宗元谓所亲曰:‘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于禹锡为执友,胡忍见其若是!’即草章奏,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州。会裴度亦奏其事,禹锡终易连州。”(《旧唐书·柳宗元传》)韩愈在铭文中认为柳宗元是“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但他肯定柳宗元的文学辞章,“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他把柳宗元的文章视为高于其为将为相之事功的千秋功业,认为其文辞必传于后。柳宗元的许多作品,诸如《捕蛇者说》、《蝜蝂传》、《戒惧箴》、《师友箴》、《敌戒》、《永某氏之鼠》之类短小精悍的小品文,令人百读不厌,迄今读来仍极有启示意义。柳宗元与韩愈之间的交往及书信往来中的情谊,也是值得后学景仰的榜样。
年谱1976年2月12日记载,毛泽东复信刘大杰,这是因为刘大杰在1975年8月2日、3日两次致信毛主席,其中问到韩愈作品在文学史上的评价问题。刘大杰在信中说:
“关于韩愈问题,仍有疑虑。现在报刊文章,对韩愈全部否定,说得一无是处。韩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严加批判。但细读韩集,其思想中确存在着矛盾。其诸多作品,如赞扬管仲、商鞅之功业等,都与儒家思想不合,而倾向于法家。再加以他的散文技巧,语法合于规范,文字通畅流利,为柳宗元、刘禹锡所推许。关于这些,如果全部加以否定,似非所宜。”
毛泽东在复信中说:“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至于毛主席在1965年与刘大杰谈话中提到的屈原《天问》、柳宗元《天对》,是他在1973年12月下旬下达给我们一批古文标点注释中的二篇重要作品,与之相关的还有刘禹锡《天论》和柳宗元最后的《天说》,那可是毛主席最爱读的作品,这在年谱中同样有记载。说来话长,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一项专门学问,本文为篇幅所限,只能留待今后专文论述了。